时间:2017-02-06 20:01 来源:凤凰读书
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副睿智深邃的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矻矻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太唯美了,太理想化了,他就显得很孤独,也很痛苦,与世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最后,也是为了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他曾对儿子傅聪说,作为音乐家,“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巴哈、贝多芬、肖邦,等等”。其实,这话正是他夫子自道,他自己就是把艺术奉为上帝。所以,他教育傅聪要把学问、艺术、真理看得一样重要,都要放在人生的第一位。真或善,不一定兼有美,而美,一定是又真又善。他曾说:“这是我至今没有变过的原则。”
显然,他也接受了米开朗基罗承袭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觉得真正美的极致是不可能存在于尘世的,只有在理想的世界中才能找到。艺术家有可能认识它。傅雷把艺术看得如此崇高、圣洁、美好,艺术家就必得怀着一颗像宗教家那样虔诚的心,哲学家那样形而上的思想,才能创造出真正达到“超然象外”“浑朴天成”“化入妙境”境地的艺术作品。
他自己无论写作理论批评文章,还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苛求到旁人看来有点不合情理的地步,这正是他那颗虔诚热爱艺术之心的自然流露和体现。如翻译家罗新璋所说,他“是以虔敬的心情来译这部书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其实,他还“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因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其“广博浩瀚的境界……的确像长江大河”。可见他对艺术美是何等崇敬热诚。就如那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我看来是具有开拓性经典意义的美术简史性质的论著,把美术历史知识,美术家的心灵活动,美术作品的深邃和神韵,娓娓叙写得那样流畅生动,本身就是一部极佳的艺术品。但当年在上海美专教课时作为讲义用过,在刊物上发表过一小部分外,他却“秘藏”了数十年,连傅聪、傅敏兄弟都从未听说过。傅敏推论是由于他以为少作,是“不成熟的文字”而“束之高阁”。其心之诚,其意之严,由此可见。还有《罗丹艺术论》这样一部经典著作,他在年轻时就曾译完全书,根本就没有与世人见过面。就是说,他从事译事时常常是不带功利目的的。至于那几部名著的翻译,他时时觉得有许多不满意处,哪怕百十万字的译文,都下决心,充分研究琢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译,甚至迂执到把旧译付之一炬而不愿留存于世。如大家所知道的《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翻译就是如此,尽管他已经“煞费苦心”,却“仍未满意”。因为他追求的是译出“风格”来,达到“神似”,这又何其难也!同样,他把那些粗制滥造、“损害艺术品的行为”,“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对“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
一般人以为只有创作才算是艺术,这是世俗的皮相之见。优秀的文学艺术批评和翻译作品本身也是艺术品。中国许多诗话、画论,都是用诗一样的形象的语言表述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欣赏的优美境界,达到情理并茂。如傅雷指出的那样,翻译就像音乐中的歌唱家、演奏家,戏剧舞台上的演员,虽然都有所本,俗谓“二度创作”,但各自都是独立的艺术创造。批评家、翻译家都要像搞创作的人一样进入角色,用自己的心灵、感情与原作融成一体,创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灵动的新的艺术世界。傅雷说他翻译《幻灭》时:“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目前可谓经常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他又说:“翻译之难,比起演奏家之演绎往昔大师之杰作,实在不遑多让。”因此,他要求“翻译应当像绘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傅雷在文学艺术批评和翻译等文化领域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和广泛的影响已为世人公认,笔者在拙文《傅雷的艺术人生》中也有所介绍,这里就从略不赘述了。但想再一次强调的是:他的著译实绩充分说明,与那些搬弄艺术教条术语的评论文字相比,与那些艰涩平庸、词不达意的译文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品格。因为他从事批评、翻译时,是一种心灵的自然流泻,是发自灵魂深处纯朴的人性的昭示,那么富有性灵,甚至力求臻于脱尽尘世烟火的纯美。他最赞赏的是汉魏文人,《世说新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是超凡入圣的,把人的本性的美最充分发掘展示。也许这种美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他经常说:“艺术之境界无穷……”“有史以来多少世代的人的追求,无非是perfection(完美),但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所以perfection(完美)像水中月,镜中花,始终可望而不可即。”话虽这么说,但他却是坚持不懈地向着这样的境界努力,这正是他醉心追求的。
所以,他既是美的创造者,又是美的布道者。当你看到他那执着痴情地诠释那些文学、绘画、音乐的艺术美的时候,很自然地会觉得他真像一位忠诚虔敬的美神代言人,只是布的是美的福音,而不是圣经里的教义。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曾动情地吟唱过“我为美而死”的歌,认为这和“为真理而死都是一回事;我们是弟兄两个”。傅雷一生献身于美,追求美,最终玉碎,也是以身殉于美。在他给内弟的遗书里,明确无误地说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当时暴力迫害的恐怖情景:最不能容忍的是,人的尊严和人格被践踏蹂躏,人的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辩白的权利统统像一块破布给扔弃了!这时的傅雷,要不在暴虐的鞭子下自责自辱、自轻自贱地苟活着,要不挺着胸膛走向死亡。傅雷曾经非常明白地宣称:“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也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尊严是人性美的重要体现,绝对是傅雷一生做人遵循的准则,是为他生平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文革”来了,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他就已存牺牲决心。
面对美的世界的毁灭,美的消失,他连过去赖以为生,相以为伴,可以躲避外面风雨的艺术角落都已不复存在;何况傅雷对美和自由理想的执着、痴情的追求本身就是超前的,不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容忍的。就像茨威格那样,因为看到欧洲陷于法西斯纳粹的黑暗魔掌下,艺术美和自由被扼杀,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傅雷则更是直接面临暴力的淫威下,只有用自己的躯体、生命作抗衡,作挑战,给予最后的一击。这不只是为一己的,而是对人类的尊严和人格的维护和捍卫,其抗议声是要永存于历史的。那时,当人们私下口口相传这个消息时,曾引发过多么强烈的深深的震撼和思索:“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与世无忤,与人无争’的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都不被容于世?”不要小看这个疑问,它在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成了承担痛苦的象征。所以我说傅雷是美的殉道者;还借罗曼•罗兰对英雄的解释,认为傅雷是一位真正的文化英雄。
我每读傅雷遗书,都使自己的灵魂震撼战栗:在那样残暴恐怖的情况下,他还能这么冷静细致,把后事一一交代,不欠这个世界一分,真个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傅雷不只执拗耿介,而且一尘不染地清清爽爽地走了,以他一生追求的美好形象离开——不!是永远留存给了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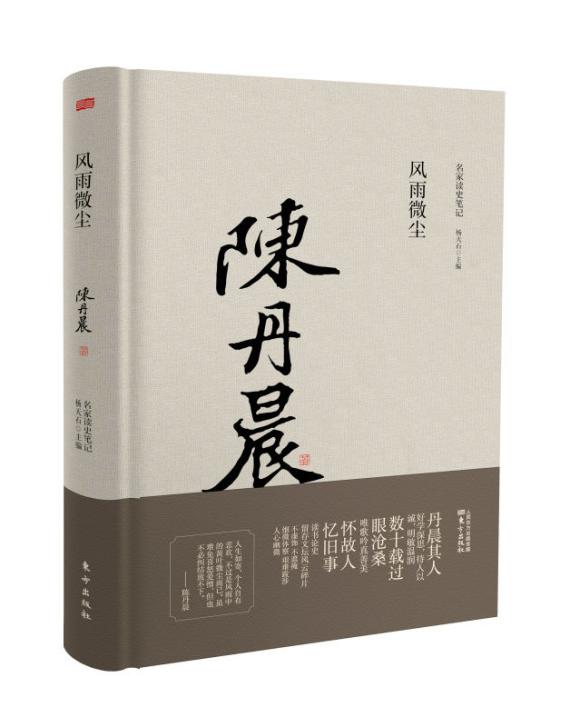
2007年8月
本文摘自《风雨微尘》,陈丹晨 著,东方出版社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商务财经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 栏目更新 |
| 栏目热门 |
商务财经网介绍|投资者关系 Investor Relations|联系我们|法律义务|意见反馈|版权声明
商务财经网Copyright©《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编号:京ICP备17060845-2